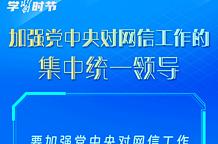生活是大树 人类如小虫奋力爬行

池莉博集天卷供图

《大树小虫》
作者:池莉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树小虫》讲述了出生于富商家庭的钟鑫涛,父母竭尽全力为其打造优裕的成长环境,终将其培养成为名校高才生,希望其继承家业。出生于高干家庭的俞思语,被爷爷奶奶众星捧月般呵护着,性格天真单纯,不谙世事。这一场看似门当户对、一见钟情的自由恋爱,却是众人运筹帷幄、通力配合的精密部署。两个人的结合,两个家族的联姻,延展出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宛如一条曲折又动人的长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张丛博实习生程贺
写人,写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这是池莉写作从一而终的宗旨。
池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写出《烦恼人生》《生活秀》《来来往往》等现实题材小说佳作,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对时代的把握很准确,能敏感捕捉到笔下人物所处年代的特质与痛点,她的小说中写到的市井人情、饮食男女凸显地域性和鲜明个性,生动、犀利,非常有烟火气。
这些写作中的特质在她这部长篇新作中得以延续。《大树小虫》从2015年的武汉讲起,两个家族、三代人,在中国社会变迁剧烈的大半个世纪中,历经出生、成长、就业、婚恋……他们的命运随时代洪流摆荡,亦或多或少受上一代人左右,更在一定程度上由自己掌握。这些出身、个性、所处年代乃至人生轨迹都不尽相同的人物,像是沿着生活这棵巨树的枝干朝着四面八方行动的蚂蚁,微小而充满活力,以时代变幻为背景,上演着充满张力又不乏悬念的人生大戏,人性的不同侧面则在一出出悲喜剧中清晰展现,或者扭曲纠结。
在《大树小虫》之前,池莉已经十年没有出版长篇小说,对她来说,这部长篇小说是在构思成熟、视线清晰,能够看透与把握上下三代人之后才开始动笔书写。以前短中篇小说快速的写法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于是她想挑战一种不同以往的长篇小说写作形式。
基于新颖、有趣、耐读、反传统结构、不对称审美、带入感强等想法,《大树小虫》在人物设置、时间跨度特别是叙事方式和篇章结构上都有不同以往的变化,书中第一章不同人物分别讲述的方式立体而多元,第二章围绕书中人物俞思语“造人计划”始末而命名的一串相同的章节名颇有荒诞色彩,多声部的叙述视角、打破平衡的章节比重是一种创新。
“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大树,人类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但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向上爬的时候整个时代其实在向下。能够在这棵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池莉这样阐释《大树小虫》这个书名。6月18日,池莉接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专访,看池莉如何写出人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
对/话/作/者
池莉:我就是要重新诉说
大河报记者:你已有十年没有出版长篇小说了,为什么会放慢写作的脚步?又是什么契机开始这部长篇的写作?
池莉:近十年前开始构思这部长篇,草拟提纲。其间写了中篇小说《她的城》《爱恨情仇》等,还写了一批诗歌与散文;在《三联生活周刊》《新民晚报》开专栏;出版了散文集《石头书》《立》《池莉诗集·69》《池莉经典文集》(九卷)。屈指一数,就我从来都不快的步伐来说,还真不算慢。专栏文章的点击量,也经常有10万+;新书印数,比如《立》,发行了近20万,其他书也都有加印。是我和媒体比较疏远、在闹市出头露面极少的原因吧,我这个人没什么热点话题,默默无声地淹没在文字的汪洋大海里了。因此,动笔开写这部长篇也不是什么契机,就是构思成熟了,视线清晰了,能够看透与把握上下三代人了,就开工了呗。
大河报记者:你在构思当中是怎么想到用人生表情来写人物、贯穿人物这样特殊的写法呢?
池莉:小说是十年前开始,年轻时候那种爆发式、喷发式的写法非常快,就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星期的那种写法。我自己都感到有一点受了惊吓,突然觉得如此熟练地炮制小说可能是件危险的事情。到了十年前,我觉得作为作家来说衣食无忧了,就应该考虑小说不应该写得那么顺手和熟练的故事,这样我就开始了对新的长篇构思的一种创造,不敢说创新,努力地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也不敢说这个就成功了,但是我真的是想努一把力,创造一个非常简明快速能够抓住读者的阅读方式,把所有的虚字能够甩掉,人生表情,就四个字给你一看,就可以有视觉感。我希望把阅读感和视觉感能够直接地沟通起来,以缩短阅读和视觉之间呈现的形象。
大河报记者:这本书跟你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文字表现非常独特,有非常多时尚的语汇,是一种新颖的、有创意的语言风格,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突破的、另类的、不同于传统方式文字特点来写这40万字的新长篇?
池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所有人物的关系不是一种模式,不存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也不存在能够确定的关系。书中的人物关系也非常复杂,如果我把老年、中年、青年各写一部,写成非常传统的故事,分开写的这种状态没有纠缠在一起,就没有那种微妙的不可对话性,没有一种微妙的痛苦。可能我的逆反发育得比较晚,在写这部长篇时突然察觉到自己的一种反叛心理:谁说汉语有一定之规,老师教给我们的语法谁说是对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关系,凭什么一定要用这些虚字?凭什么我这句话一定要平铺直叙?我就是不,我就是要乱,我就是要重新诉说。
大河报记者:书中人物在中国社会多是中上阶层,但似乎没有哪个人物过得快乐,更多是压抑、焦虑、纠结的情绪,你所理解的这些人物“不快乐”的根源是什么?
池莉:用科学眼光看这个问题会更清楚:快乐指数并不与物质拥有成正比。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财富与社会的比例关系,更没有认识无私奉献的真意,随着个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人与人之间自然会产生更多矛盾,这些矛盾当然会带来更多压抑、焦虑、纠结和烦恼乃至痛苦。
大河报记者:既然写了几代人的故事,自然涉及亲子关系,你如何理解在中国这几十年飞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亲子关系的变化?
池莉:亲子关系与其他人物关系一样,处于哪个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这几十年的飞速发展,速度太快,竞争太激烈,亲子关系根本都来不及适应和调整,只能无奈地直接压缩在培优班里、厚重大书包里、中考高考里和就业里,紧接着就张罗优质资源婚配,张罗房子车子,张罗优生优育,新一代出生然后又是新一轮紧张生活开始。其实人们都知道,亲子关系应该拥有更多闲适时间和空间,彼此共享爱意亲情、用心关注对方喜怒哀乐、扶老携幼交心谈心互为生活语境,以生命的愉悦与健康为终极目的。但是社会环境给家长们造成了一种心理恐慌,以为在千军万马拥挤的独木桥上,不拼命往前挤,就会落后和输掉。
大河报记者:武汉为你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搭建了一个舞台,但也存在物极必反的情况,地域会不会也限制你发挥某些东西呢?
池莉:作家和作家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特意要写这个地域,没有以写这个地域为目标或者为目的。在我看来,作家和地域是这样一种关系,任何人都有自己特别熟悉操作的一种符号、语言方式。长期在武汉,你只会说武汉话,你知道武汉话它能够最形象地来完成你对这个人物的表达。武汉话里面的虚字就非常少,而且特别精练。在下雨我们会说“在下”,毛毛细雨会说“在纷”,再就是“完了,天塌了,泼下来了”这三种状态,毛毛细雨、在下雨、倾盆大雨,我们不会用书面语言和老师教的语言。我写小说最重要的是动词,除了动词还是动词,我觉得一个动作一句话当中一定要有动词作为骨架,所以武汉话里面的动词特别多,虚字特别少,这就是一种原因,不是我一定要写武汉,是我操纵这种语言来完成我自己的表达。
编辑:郭同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