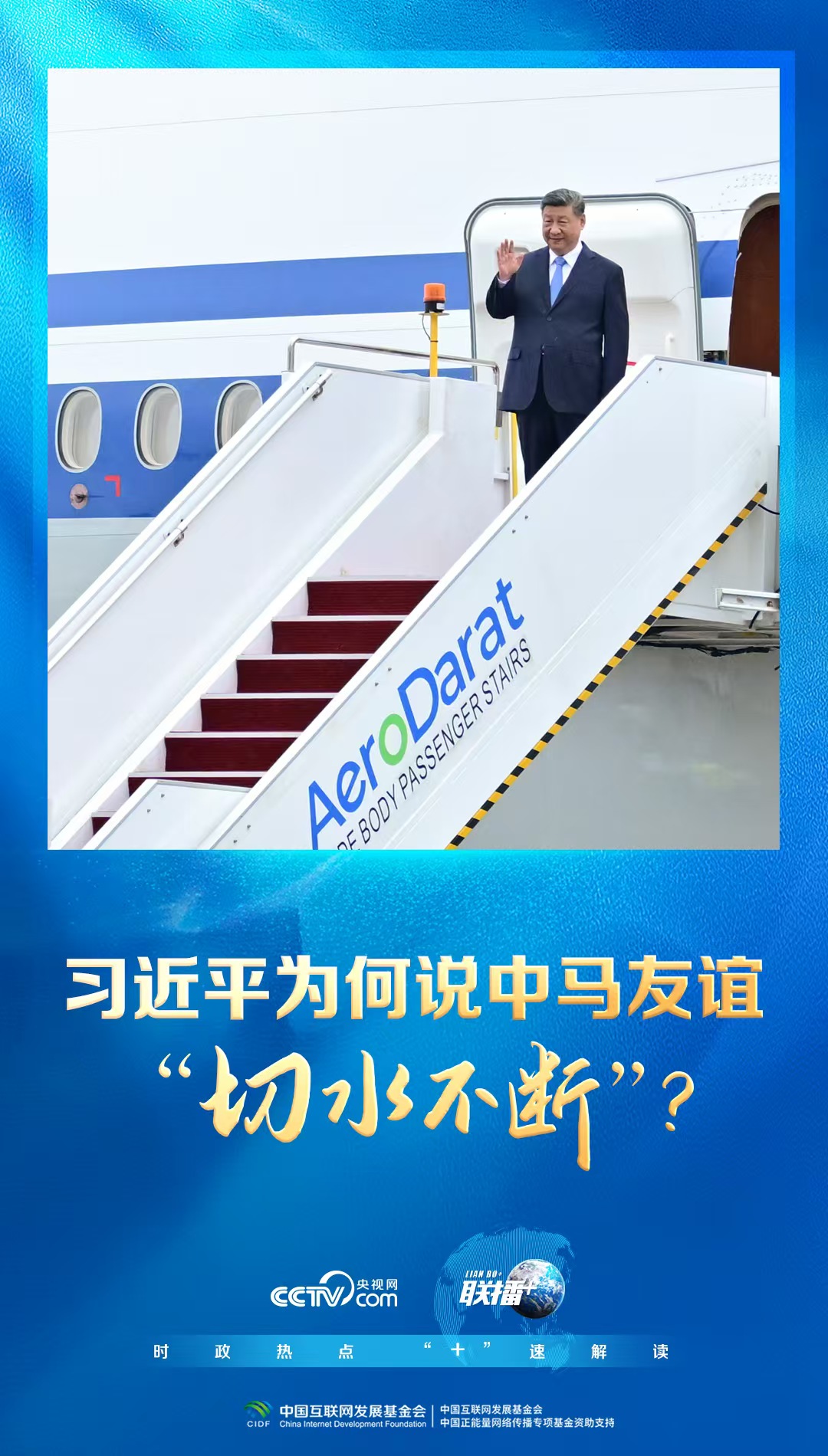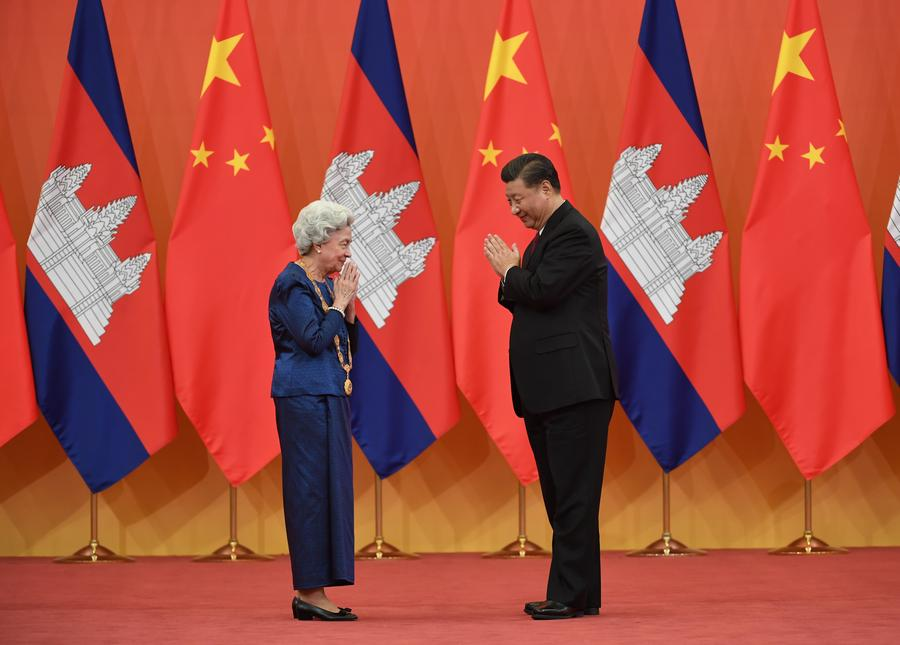在新媒体时代与鲁迅相遇


ChatGpt制作的鲁迅照
(1/2)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在去世前一个月,鲁迅先生留下了七条遗嘱,其中一条是:“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先生不会知道,在他离开89年后的今天,许多人的生活被学习、工作和刷短视频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但我们没有忘记他,相反,先生的作品、文字,比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广,堪称当之无愧的文学顶流。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是如何与鲁迅相遇的?又是如何运用新媒体对鲁迅进行阅读、传播和重塑的?鲁迅在我们与新媒体时代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与众不同的作用?如何理解这其中的“鲁迅热”现象?又应当如何建立与鲁迅的联系?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黄海飞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彬老师和西北大学文学院张宇飞老师的支持,他们将自己的大半精力,放在了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和传播鲁迅上。希望我们能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共读鲁迅,那里的世界与你我都有关。
当代青年与“网红鲁迅”
刘彬
近年来鲁迅忽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火起来,B站、微信、微博、小红书、知乎等APP上处处可见与鲁迅有关的图像或文字,弹幕区、评论区、表情包中时时都有对鲁迅的征引或玩梗。以鲁迅为素材或对象的短视频、歌曲、漫画、帖子、有声书等遍网开花,形式既花样百出,主题复变化无穷。仅以见于B站上的短视频为例,就有翻唱歌曲《起风了》而礼赞鲁迅生平业绩的,有以rap形式表现《野草》《狂人日记》等鲁迅作品的,有以鲁迅与周树人为二人而一逗一捧说相声的,有以电视剧《觉醒年代》《楼外楼》中的鲁迅形象搞二创的,甚至已有用最新的AI技术复活鲁迅开口说话的,不一而足。这些视频或严肃或戏谑,播放量都极可观。虽然自有网络以来,就有所谓“网络鲁迅”的产生,但似这般“千树万树梨花开”,并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却似乎还是头一遭。
创造了这一网络奇观的主力军,是以大学生为主的当代青年群体。这是非常有趣而耐人寻味的现象。多年来,鲁迅虽然始终是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常客与重点,但也因为考试变成学生们惧怕的对象。然而,偏偏是“怕周树人”的孩子们长大后借助新媒体平台与新技术手段,自我更新了他们的鲁迅印象。在他们半认真半游戏的“玩转”中,总是横眉冷眼的“鲁迅先生”变成了亲切好玩的“迅哥儿”。从避之唯恐不及到玩得不亦乐乎,他们前所未有地亲近鲁迅。他们以新媒体的逻辑和力量,将鲁迅打造成了“流量大咖”,激发了更多人看鲁迅的兴趣。在近几年与学生的交流中,我多次听到他们描述,是与“网红鲁迅”的遭遇,让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鲁迅的可爱之处。
课堂里的鲁迅令学生敬畏,网络上的鲁迅却让学生热捧,这足够作为老师的我们反思的了。我并不认为将鲁迅“玩”成网红是一种不敬或亵渎,相反,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在以新的方式向鲁迅致敬,邀请鲁迅进入他们最熟识而乐居的虚拟空间,并且在事实上帮助重新扩大了鲁迅的社会影响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鲁迅逐渐走下神坛而退隐学院。尽管学者们对此有所警醒与反思,但似乎无力改变这一趋势,而鲁迅若失去社会价值而仅存知识价值,那就真真叫人失望了。因此,与新媒体相遇而大放异彩,于鲁迅而言,无异于在学院或知识圈外的一次重生。
今日新媒体上“鲁迅热”的一大特点,是呈现和放大了鲁迅的好玩。虽然对于学者们而言,鲁迅由“神”降而为“人”已是与我们拉近了距离,但对于新生代青年们来说,鲁迅得更进一步是好玩之“人”,才能吸引他们亲近。他们以其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使鲁迅好玩了起来,由此开启了进入鲁迅世界的新路径。任何作家或作品要想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就必须能够接受后世层出不穷的新的诠释方式。借助新媒体手段使鲁迅与其作品好玩起来,并因此使其得以重返社会,无疑是一种赓续鲁迅文学生命的创举。这一创举是如此之受欢迎,以致线上的“流量大潮”甚至带来了线下的“经济热潮”,主打鲁迅元素的文创产品如帆布包、钥匙扣、手机壳、卡通玩偶等纷纷热卖。当然,看到鲁迅好玩也许只是看到皮毛,但对于无不经过“怕周树人”教育的人们来说,若无忽然看到好玩这一步,恐怕也难有回头重看那一步。
新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多元自媒体的涌现。因为有了自媒体,普通大众不再只是信息或事件的被动受众,而是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参与或制造事件的主动权。这就使得传统媒体的中介性和权威性不再唯一。鲁迅在自媒体上的走红,正是青年们越过包括中小学老师在内的权威的中介,自发创造并自我增殖的现象。换言之,这是当代青年选择直接与鲁迅对话并“发现”鲁迅的体现。鲁迅生前最重视青年问题,最喜欢与青年为友,最反对青年寻求导师,主张青年自己联合起来去开辟新的生路。当代青年之举无疑跨越时空而契合或响应了鲁迅的倡导,因而是深得鲁迅之精神,堪为鲁迅之朋友的。正因为他们选择以鲁迅为朋友,而非以鲁迅为导师,他们才拆解了历来中介所形塑的令人生畏的鲁迅像,重建了他们觉得可亲可敬的鲁迅像。这其中有他们的主体性的体现,而主体性正是鲁迅最期望于青年的。我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认为,即使高估“新媒体鲁迅”的价值,亦不为过。
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追踪到青年们聚集的虚拟社区中来了。他们选择入驻各类新媒体平台,选择以青年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耳熟能详的话语与之交流。新媒体自带的弹幕区和评论区,不但使平等而即时的互动成为可能,甚至成为最被双方期待之事。象牙塔里的导师摇身一变成了新媒体上的朋友,青年们对此显然是欢迎的,而这也显然有益于革新或丰富学问的传承与推广之道。不是导师引领了青年,倒是青年引领了导师,这是新媒体造就的值得称颂的奇景,也是合乎鲁迅期待的进化之路。总之,对于发生在新媒体上的“鲁迅热”现象,我以为与它所显示的新媒体的变革之力同样甚至更加值得珍视的是,它所显示的当代青年们的主体性与创造力。鲁迅所谓“将来必胜于过去”的希望正在于此。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新媒体时代的“鲁迅热”现象
张宇飞
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抖音、快手、B站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已然迈入了新媒体时代。这些新媒体形式不仅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还推动了互联网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剧烈变革。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其“民族魂”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符号。在新媒体时代的语境下,鲁迅逐渐从传统“教材”走入“互联网”,其作品与思想在新媒体平台被重新激活,经典语录常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中,笔下的人物形象也被搬到了社交平台中,换言之,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中已经掀起了一股“鲁迅热”。那么,作为生活在新媒体时代却又常常关注传统鲁迅文学的新青年们,应该如何理性且辩证地看待新媒体语境下的“鲁迅热”呢?
首先,这种“鲁迅热”现象对于向大众尤其是向青年人普及鲁迅文学与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例如,B站曾将鲁迅《野草》中的16篇散文诗改写成了说唱音乐,选取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野草:插图本》作为视频背景,用一种新潮的方式呼吁大家重新感受鲁迅文字的力量,这无疑令众多网友开始关注并阅读鲁迅生命哲学的代表作《野草》;由“碟子”作词、“十年少”演唱的《呐喊》视频也用说唱的形式表现出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营造出的“铁屋子”的形象,并将小说集《呐喊》中的多部作品及其背后折射的启蒙与批判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有助于未曾深入涉猎过鲁迅作品的年轻人关注鲁迅的文学创作。再比如,由于鲁迅文学在中国长期具有巨大影响,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其不少“金句”已成为社交软件里的表情包,“横眉冷对千夫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从来如此,便对么”“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等都是其中常见的语句,这些表情包幽默地传递了鲁迅思想中的犀利与尖锐。固然其中也有不少句子是对鲁迅经典语录的改写或恶搞,但并不妨碍鲁迅思想的传播与普及。毋庸置疑,新媒体时代下的“鲁迅热”不仅打破了学院与大众的壁垒,使传统的经典文本与当下的数字文化进行碰撞,既降低了作品阅读与文学接受的门槛,还吸引大量的鲁迅爱好者成为“粉丝”,同时借助“流量密码”最大程度推动了鲁迅及其周边的普及化。仅上述的《野草》说唱视频,在B站等各大社交媒体上的播放量动辄超过100万,可见在新媒体时代的语境下,传统的经典作家鲁迅能够用更加轻松的方式与读者接触和见面,这不仅反映出鲁迅思想在新媒体时代下仍旧具有魅力,也说明新媒体软件可以借助众人的智慧进一步吸收、理解、阐释与传播鲁迅文学。
与之相对应,除肯定新媒体语境“鲁迅热”的积极意义外,我们对其也应持有一定程度的谨慎态度。虽然自媒体传播者采取了不少更加新颖的方式传播鲁迅的生平及思想,但这种传播由于缺乏权威性与专业性,难免浅薄化、符号化、庸俗化、碎片化、娱乐化,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等硬伤。例如,采用鲁迅金句的表情包就常常为适应当下的社交环境而改动鲁迅的原文,使得新的表情包与鲁迅的原意谬之千里,这种改动本身无可厚非,但很有可能将错误的信息传递给青年读者,不利于他们理解鲁迅文本产生的语境与背景。此外,新媒体时代下的社交软件一般都具有“短平快”的传播特点,这种传播方式虽然具有传统媒体不能比拟的优点,但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上述弊端,可能导致信息缺乏严谨性和完整性,甚至出现误解和传播失真,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削弱读者的思考能力。面对本就思想深刻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鲁迅文学及思想,如果不能系统性地了解鲁迅的生平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不能深入了解其文学与思想的来龙去脉,甚至不能了解其特定语境下的语言风格,只是凭借新媒体软件的部分快餐式解读来认识鲁迅,则极有可能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甚至对普及鲁迅文学与思想产生危害,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由此可见,如何平衡社交媒体的娱乐传播与传统媒体的专业阐释,是新媒体语境下鲁迅文学与思想传播所要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的知名作家,其批判、反抗、斗争、牺牲的精神深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符号与标签。鉴于鲁迅本身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在新媒体时代的语境下重新建立与鲁迅的联系时,应当将鲁迅的经典文本、固有思想与当下的传播环境相结合,一方面采取新的传播方式,将鲁迅小说改编为歌曲、漫画、动画或互动游戏,突破传统的传播媒介,以更贴近年轻群体的方式普及鲁迅的生平、创作、思想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应该想方设法构建具有专业性的讨论平台,避免陷入信息化的陷阱,避免出现常识性的错误,邀请专家、学者与普通网民共同参与新媒体时代语境下的鲁迅传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重审鲁迅的当代价值。作为中国的国民作家,鲁迅的作品可谓经久不衰,常读常新,新媒体时代出现的“鲁迅热”归根到底在于其文学的魅力与价值,在于其思想对于我们民族的开导与启迪。进入新媒体时代,鲁迅文学与思想的传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只要正确把握鲁迅的立人、启蒙、批判国民性等思想内核,灵活运用新媒体工具重构传播方式,必定会持续这场新媒体时代的“鲁迅热”。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人工智能时代鲁迅的“轻”与“重”
黄海飞
年初DeepSeek引发全民关注,一周之内用户突破1亿,成为史上最快达到这一纪录的应用软件。DeepSeek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与春晚舞台上的宇树机器人一起将中国拽入了AI时代。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那么,AI时代还需要文科吗?与鲁迅相关的追问是,AI时代,还需要鲁迅吗?鲁迅将会怎样?
鲁迅生前没有留下任何音频和视频资料,这令后人稍感遗憾,然而AI视频技术可以仅凭一张照片就让鲁迅“原地复活”,你可以看到鲁迅的动作,听到鲁迅的声音。鲁迅在此变得轻盈可触了。这像一个悖论,非人的AI却使鲁迅更像真人。但这实际上延续了社交媒体时代以来的趋势,一种我称之为“轻鲁迅”的趋势。自2009年微博上线,2014年微信推出,社交媒体上开始涌现众多将鲁迅描述为轻松活泼形象的文章,如写鲁迅吃柿霜糖吃到牙疼,写鲁迅爱看电影爱坐小汽车,写鲁迅爱好美术爱搞设计,多才多艺,鲁迅是个吃货∕文艺青年∕斜杠青年∕北漂青年……进入短视频时代,B站上鲁迅成为顶流,至今已有三个视频播放破千万,分别是“【亿万填词】我把鲁迅先生填成了一曲《起风了》——谨此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野草》:我把16首鲁迅写成了一首歌”“悬溺一响,鲁迅登场”。三个视频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即鲁迅的生平或者作品被改编成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歌曲。鲁迅不再是正襟危坐、怒目圆睁的斗士,一变而为和蔼可亲、爱玩爱笑爱打闹的年轻人亲近的形象。概而言之,鲁迅走下神坛,回到人间。
这首先当然是对于长久以来鲁迅形象的丰富。一直以来,鲁迅的简介沿用这个定义:“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化新军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在实际讲授中,可能又偏重于革命家。而在课堂之外,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得以发现别样的鲁迅。
年轻人看待鲁迅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不同于上辈人的仰视,他们更多是平视。鲁迅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偶像,而是可以握手拍肩、平等对话的朋友,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一点倒更接近于鲁迅在世时的状态。那时候左联内部年轻人就有不同的声音,甚至平易地将鲁迅称为“老头子”,非左翼青年的观感则更具历史现场感。最近读王世家所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卷中收录了马钰所写的《初次见鲁迅先生》,初刊1926年3月《孔德学校旬刊》。马钰当时还是十五岁的中学生,文笔稚气诚实,谈及自己最爱看鲁迅先生的小说,因为“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写到初次见鲁迅的印象,先是从玻璃窗外一看,“只见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写鲁迅衣着,“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写鲁迅吃东西,“看来牙是不受什么使唤的,嚼起来是很费力的。”写得都非常得真实,不过分拔高也不肆意贬低,鲁迅在其笔下只是一个普通人。时间跨度将近百年,年轻人对于鲁迅的视角与看法竟惊人的相似。
回到当代,这种将鲁迅轻松活泼化的描述对于鲁迅的接受自然是很有裨益,年轻人借此才得以亲近鲁迅。然而,当过于强调鲁迅轻松的一面,我们或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鲁迅的另一面,即沉重的深具批判性的鲁迅,后者才是鲁迅的意义所在。很遗憾,在上文提到的B站热门视频中,这些元素展现还不够。
也不是没有反例。我一直关注B站UP主“云社”,从它取名即可见其幽默与讽刺。“云社”让鲁迅与周树人说相声,将鲁迅的“轻”与“重”演绎得恰到好处。看到这样的视频,你又会觉得AI时代,鲁迅还是光芒万丈,鲁迅仍将不朽。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王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