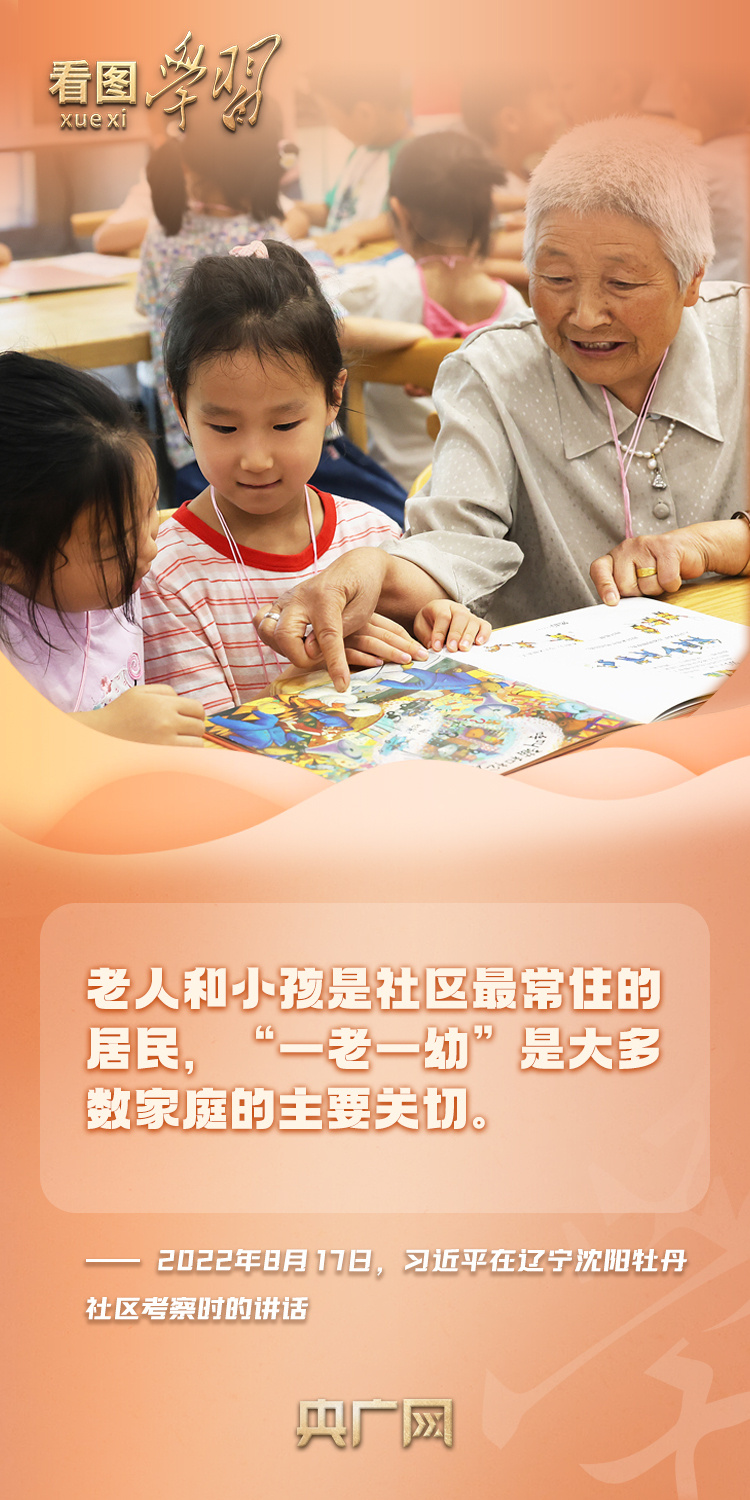在寂静中,倾听灵魂的声音

孙惠芬
告别《紫山》的写作已经半年有余,可写作时的感受一直都记忆犹新。我像一个毫无准备的历险者,被笔下人物带到一个又一个场景,一次又一次陷入沼泽,眼看着就要抓住一根稻草,稻草却不翼而飞,眼看着就要爬到彼岸,彼岸在一瞬间又变成了此岸……
说毫无准备,其实是有备而来,为了这部小说,我准备了近十年。2011年,我随大连医科大学团队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曾了解到一个家族内三人因情感纠葛而轻生的案例。
这是一个有关人类道德难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爱与恨、道德与罪恶,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虚构作品中进行深挖和探讨。可是十年过去,我一直都没能动笔。或许有些作品,除了艺术储备之外,还需要年龄和经历作底——在我这里,艺术储备从来都没有游离在经历之外,它是与人性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而在人性这个幽深隐秘的未知世界,年轻时,我能触及到的可能只是表层,触及不到更深邃的东西。
在我早期的作品《歇马山庄》《上塘书》和《吉宽的马车》里,我想我写出了乡村人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写出了人性的困惑和迷惑,但却很少触及罪恶,很少触及沉沦之后的觉醒和超越。即使2011年有那一次访谈的经历,了解到那些遭遇苦难的人往往会陷入因与果的追问,从而精神世界会有一次意想不到的超越和上升,写下了《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和《寻找张展》,但关于人性的救赎和建立,只碰触到冰山一角。那片精神高地在作品里,仅仅是一束光,就像透过窗口照进来的光。
人性的建立,需要你对苦难有着深度的体悟和洞察,对人性有着深度的悲悯和同情,它需要你跳脱智力,不是用脑袋,而是用心,因为只有心才是智慧的根,才会照亮黑暗。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里写道:“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等待了十年,我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等待什么,只知道有一天灵感降临,我发现陷入沼泽的三个人向我走来。
这三个人背后,涉及到的正是人性的觉醒和超越。灵感告诉我,这一次,我不是去触碰冰山一角,而是冲着冰山而去,去钻探这冰山的全部。实际上,在等待的十年里,我一直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传统文化经典,或许正是先贤们的古老智慧激发出的思想,照亮了《紫山》。我的创作激情全面爆发,我对这样的写作充满期待。我的年龄,不是尤瑟纳尔说的四十岁,而是六十岁,叠加了岁月带给我的种种经历。为写好《紫山》,我无数次下乡走访,鲜活的故事记录了三大本,而在此之上,竟有两本厚厚的思考笔记——那是有关人物所处时代、出生家庭、性格特征的一些碎片化的分析,因为昨天的想法总被今天的想法推翻,所以写得很长。我期待着合上笔记本的一刻,这也是我每一次写作都要经历的时刻——只要笔记合上了,写作就开始了,写作一旦开始,笔记便永无翻开之日。
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我沉潜进那道想象世界打开的裂缝,似乎是纵身一跃就跳了进去,我希望自己捕捉到笔下人物每一个瞬间的表情,可令我想不到的是,我越是要深入进去,越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人。在我的笔记里,他们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有的连影像都没有,但当三个人锁定在那特殊的场域,人物一个个来了。他们不光来了,还发出了确定的声音。
这注定就是一场艰难的写作,它的艰难在于,我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紧贴人物,与他们一起经受灵魂拷问,感受炙心烙肺的疼痛与觉醒,一方面需要倾听包围过来的各种声音——一桩与情感有关的悲剧事件,无疑要搅动起一座古老的村庄,当沉寂的乡村大地得以苏醒,那些沉默的人群脚踩大地、仰望苍穹,却深藏着种种隐秘的心声不得诉说,他们想通过我发声。
这正是小说写作最神奇的地方。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我看到我笔下的世界在重新组合,可这么多男人女人向我涌来,我根本想不到。这使我常常陷入失语状态,因为当我凝视他们,看到他们欲说还休,常常不等下笔,情感就汹涌而至,而当我感情的通道有泪水涌动,修辞的通道顿时就拥塞狭窄……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让自己长时间沉入寂静,在寂静中,去倾听那些灵魂的声音。
在寂静中倾听,用心,而不是用脑,这或许是《紫山》得以完成的重要秘诀。
不由得想起16岁那年的一个场景,当时海城发生7.3级地震,辽南的村庄震感强烈,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我和家人都住在搭在外面的草窝棚里。那样的夜晚,我专注在窝棚里的小世界,听着父母、奶奶惆怅的叹息,想象要是大地裂开一道口子,把村庄吞进去,而我和奶奶、父母还活着,我们该怎么办?有一个晚上,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地震没发生,我们还活着,我将来一定要写一本大书,写掩埋在地下、没有机会发声的父母、奶奶的心声。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作家,那时候,也并不知道苦难为何物,更不知道在苦难中,精神世界里会有怎样的变化。但那时候,我强烈地知道,普通人的内心,最需要去书写。
实际上,在写作中,那些向我走来的小峪沟人里,就有我的奶奶、父亲和母亲,就有我的父老乡亲。或许他们经历的生活是别样一种,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在时间里熬过。
实际上,是跟随他们在时间里熬过,我才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当然,在寂静中倾听,你听到的一定是自己灵魂的声音,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可以和更多人相遇,才有可能了解他们内心生活的全部。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
编辑:祝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