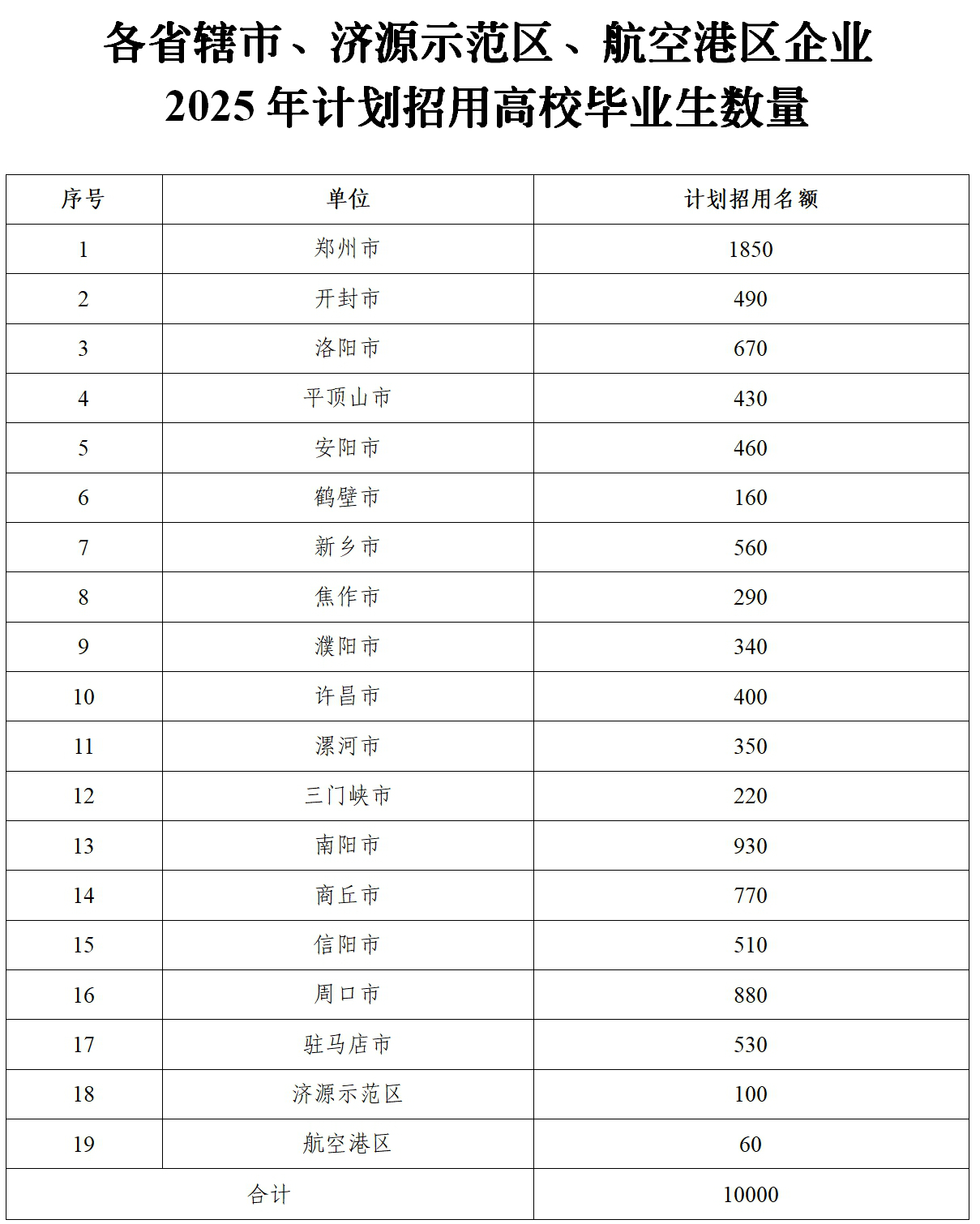烽火中的文艺担当——抗战文艺的民族记忆与时代启示

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

天蟾舞台五月二十五日《抗金兵》戏单
(本文配图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版画)
彦涵作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艰难的烽火岁月里,一部部文艺作品吹响战斗的号角,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中华民族镌刻下精神的丰碑。80年间,战火虽已远去,但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不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持续推出精品力作,多维度展示伟大抗战历史和伟大抗战精神。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本版今起开设“烽火记忆·时代回响——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栏目,品读抗战文艺经典与新作,介绍抗战80周年主题展演展览等活动,唱响中国文艺史上的民族强音,为新征程凝聚前行力量。
——开栏的话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结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担负起唤醒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文艺抗战使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自建院伊始,便汇聚了王曼硕、王朝闻、张庚、葛一虹、贺敬之、李元庆、马可等一大批具有延安鲁艺背景的艺术家与学者;在传承延安鲁艺精神的基础上,持续积累并整理了一大批极具历史价值的红色艺术文献与作品,其中有一批珍贵的抗战文艺典藏。
7月16日开幕的“烽火艺魂——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就展现了这批典藏。展览共设“战歌震山河”“兰台唱金戈”“刀笔砺丰碑”三大板块,展出145件套抗战时期音乐、戏曲与美术领域的珍贵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彰显出抗战文艺工作者以艺魂点燃战斗烽火的家国担当,再现中国共产党凝聚民族力量奋勇抗争的壮阔史诗。
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的诞生
1939年春,冼星海读到光未然创作的400多行长诗《黄河颂》,深受感动。他在短短六昼夜内,融合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全曲的创作。作品以黄河的形象唤起民族共鸣,通过音乐语言展现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精神,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战歌震山河”展区陈列有冼星海多件创作手稿、日记以及使用过的钢笔、小提琴、钢琴等珍贵遗物。其中,特别展出了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仅有的存世手稿——1939年“延安稿”与1941年“莫斯科稿”。这两份手稿忠实记录了作品的构思与修改历程,于2003年同时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黄河大合唱》共8个乐章,通过合唱、独唱、朗诵等的综合表达,刻画了中华民族从苦难中奋起的群像。冼星海在1939年的创作说明中坦言:“《黄河》的作法,在中国是第一次尝试,希望得到鼓励以后,更努力去创作。”
“延安稿”以简谱记谱,用粉连纸抄写,共66页。乐队编制依据鲁艺音乐系当时实际条件而设,使用了当时在鲁艺所能找到的所有乐器,包括笛、口琴、三弦、二胡、竹板、木鱼、钹、铃、鼓等民族乐器和小提琴、吉他等西洋乐器,此外,为了补充乐队低音声部和烘托氛围,还自制了一些极为特殊的“乐器”,形式朴素却极富表现力。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以简胜繁的战时艺术智慧。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由邬析零指挥抗敌演剧三队首演,引起强烈反响;5月11日,在“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合唱团、配以中西混合乐队,再度演绎该作。
1941年,冼星海在苏联战火中加工、修订该曲,形成篇幅达202页的“莫斯科稿”交响合唱,采用五线谱,增加序曲,并配备庞大的管弦乐编制,更趋恢宏。这两个版本皆由冼星海手写成稿,此次展览中首次并列展出,为公众呈现了冼星海创作、修订《黄河大合唱》的全部历程。
抗战时期新编历史剧与梅兰芳的艺术坚守
梅兰芳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中国近现代戏曲发展史上,他不仅以卓越的艺术造诣蜚声海内外,更在民族危机面前,表达了坚定的爱国立场与道义担当。
“兰台唱金戈”展区聚焦梅兰芳“蓄须明志”的铮铮风骨,展出了梅兰芳《生死恨》《抗金兵》的唱片以及一系列抗战期间抗敌演剧队的文献实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鼓舞抗战,梅兰芳在上海连续赶排《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抗金兵》取材自南宋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率军抗击金兵的史实,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在淞沪抗战背景下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生死恨》根据明代传奇《易鞋记》进行改编,讲述了北宋时,金人南犯,程鹏举、韩玉娘先后被金将张万户掳作奴隶,随后历经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1936年在上海首演。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地痞、流氓经常到梅兰芳家中纠缠骚扰,要他上舞台演戏。梅兰芳借赴香港演出之机,在那里住了下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很快陷落敌手。梅兰芳看出这次难逃虎口,就以留胡须为由退出舞台,拒绝为敌伪演出。
抗战期间,梅兰芳保持了一个艺术家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在1945年10月10日发表的题为《登台杂感》中,袒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可是在战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底下,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
当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出,梅兰芳高兴得当天就剃掉了胡须,不久重登舞台,庆祝抗战的胜利。
延安精神与中国现代木刻的红色基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在建所初期,便汇聚了一批具有延安鲁艺背景的美术研究者与创作者,积累了一批抗战主题的美术藏品。
“刀笔砺丰碑”展区呈现了沃渣、力群、彦涵、李桦等延安鲁艺木刻工作者抗战期间的作品。艺术家们以黑白对比、刀刻语言,记录战时现实、激发民族斗志,不仅形成极具穿透力的视觉风格,也发展出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新兴木刻形式。
以力群版画绘画语言的变化为例,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力群有意识地思考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为劳动群众所接受,他从中国画、湖南印花布、延安剪纸、汉代画像石、仰韶文化彩陶乃至金石文字中广泛吸收营养,推动了民族形式在版画中的重构与转化。
木刻不是简单的“写实”,而是以农民、母亲、士兵、土地等意象书写的抗争。正如沃渣《劫狱》《饿死也不被汉奸收买》《卢沟桥抗战》《全民一致的力量》《恐吓》等作品所展现,那些扭曲的肢体、怒吼的口型、泪痕斑斑的面容、果敢的人物造型和遒劲的刀法控制,饱含激情,有力控诉了侵略者的残暴,赞颂了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
木刻以其强复制性和高传播性,成为抗战期间动员民众、传播思想、鼓舞士气的重要视觉武器。诞生于战火中的木刻作品,大多以描写人民疾苦和宣传抗战为主,这些作品所承载的现实关怀与人道精神,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亦是延安鲁艺精神在当代的历史回响。
艺术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产物,而是民族精神的书写者与人民情感的表达者。在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中,艺术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始终与人民生活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
在“烽火艺魂”展览中,我们得以清晰勾勒出不同门类艺术在抗战岁月中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与精神担当。这些艺术形式在功能上指向人民,在结构上追求融合,在表现上贯穿现实批判与精神动员,形成了中国红色文艺传统独有的“形式解放”与“社会归属”双重特征。
今天,回望这些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典藏,能够激励我们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融入艺术研究、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中,不断书写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时代创作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编辑:张龙(小)